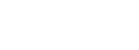献给Jean-Claude Schaetzel医生 [2]
他非常善于陪伴在他的分析者身边
并且一步一步地推进分析。
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自从 Guy Flecher 邀请我来给你们讲话以后我就想你们。
你们带给我很多麻烦!
真的!
在这次邀请之前,你们对我来说是未知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感谢 Lacanchine.com 这个网站,我才知道你们的存在,并且似乎精神分析可以让你们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在这个网站上的讨论里面听到任何东西,也没听到任何似乎是来自你们的激情。
我不时在那里读些文章,正是在那里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了。
实际上,我对我们两种语言之间遇到的翻译的困难很感兴趣,因为看上去这些困难每次都与对你们的每一个词来说永远不可能真地切断的意义的无限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且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显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此外,这些翻译问题似乎更多是与你们的语言相连,因为我们可以在汉英或汉德方面发现同样的问题。
因此我对这感兴趣,然而……如同我对诗歌感兴趣一样。因为诗歌常常紧贴事物,并且它使我思考。你们看,我不是以无足轻重的方式来用“思考”这个词的。用这种方式,我没有听到某种形式的精神漂泊,如同在世上的某种缺席,倒不如说是听到了对存在的真正呼唤。况且我认为这个呼唤是我出现在这里的动机之一,我很少离开我的国家。
因此我再说,关于你们的语言的这个奇特报告来自当我看到它似乎能够以局部的方式,例如一个词,表示如此多不同的东西时深深的惊奇。根据你们的翻译者,它似乎每次都对非常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义(significations)开放,以至于当意义(sens)被它承载时,它在每个句子中都把意义(significations)投入疑问和困惑的深渊。以至于我自问,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这种语言能产生什么样的无意识?!而且对我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这个行为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
以这个兴趣为背景,对你们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机会,来在我开业35年以后对我的实践做个小结。当然我可以在别的任何地方做这个小结,然而不论如何对我来说这底下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这个如此困难的翻译问题在我看来总是如此地不确定和冒险。
我对被那种语言占据的你们讲话,完全无法知道你们是否能听懂我的话,不是因为压抑的效果,而是因为如此完全不同的一种言语的效果。就是,这值得一试。
值得尝试对你们讲话,因为尽管有所有这些困难,我还是保留着你们能从我对你们讲的东西中听到什么的希望,而这就与我讲话的目的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可以断言你们就是我自己的通过。而且因此你们是我的通过的评委会。
因为,如果你们能听我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一起谈话,这就将是对某种实在的神圣胜利,而且我是在拉康的意义上说实在这个词的。如果你们愿意,我随后就在我们的讨论中解释对“实在”这个词的使用。
因此,在这个通过的框架下,我来这里是为了了解我们是否能够相互理解,是否能够通过我们共同的经验——精神分析——来学到些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从很好地被定义的基础出发,并且确保我们分享它,我应该把我通过精神分析这个词所听到的东西说清楚,因为正如孩子们所说:“从我开始。”
首先,这是一个经验,是我们称为精神分析的经验的东西。
它从最开始就是可重复的。
带着这两个性质,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和“科学”有关——至少是在这个词语的惯用意义上。
然而为了这个经验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这也是弗洛伊德的梦想),它应当每次都给出同样的“结果”。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按照一个实验设置的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判断科学的话,那么这就不适合精神分析的情况,因为恒定的实验设置每次取得不同的结果。当我说“结果”的时候,我说的当然是临床结果。因此每次结果的不同似乎就取消了精神分析作为科学的资格。
然而!然而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放弃使精神分析成为科学的抱负。
我向你们讲述一个众所周知的轶事来向你们展示这个抱负。一天,荣格找弗洛伊德讲他和一位女病人的麻烦,他对和这位女病人上过床非常不安。回应他的不安时弗洛伊德对他说:“在实验室中可能会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故(爆炸?),然而因为实验的有效性,这不可能重新开始。”这个显得真实的意见经常让我思索良久,因为它夸张地描绘了弗洛伊德要把正在创造中的精神分析放在他那个时代实验科学的框架下的极端努力。
既然这项事业的科学特征不涉及它的临床后果,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相信它自身支撑在实验设置上。然而弗洛伊德总是说,相对精神分析进行来说的客观实际需要而言,这个设置更多是与他自己和他的舒适相连。况且我们知道,在晚饭后他和他的弟子们在维也纳的赛马场散步的时候还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说,他自己都没有把成为一门科学的抱负依靠在实验设置上。
因此假如精神分析和科学有关,我们可以说,这既不是在它的设置层面上,也不是在它的产物层面上。
然而……
然而,我再重复一遍,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放弃关于精神分析的“结果”的科学性的这个抱负。同样,鉴于遵守“自由联想”原则所编织的自由言论,他总是断言,每个分析者都能够把他、弗洛伊德正在建造的理论化为乌有。
弗洛伊德的这个要求——把每个“个案”都视为第一个,同时这个个案也可以取消他直到那时为止所得出的所有结论,给了我们这第一个问题的钥匙。
弗洛伊德在科学的法庭上传唤的东西,正是他的理论。
这是他从被他的一个女病人称做“谈话疗法”的经验开始建造的理论。
这并不平凡。一个替代与可重复的科学行为同名的科学的理论。
为了理解他的胆量,或我们想要的他的勇气,我们需要再浸入一下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气氛。我提醒你们,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领域里,量子理论刚刚开始获得它的地位,从如你们所知的时候起变得成熟。然而,这个量子理论以某种方式终结了除纯数学模式以外的现实之客观的或甚至是想象的表象的所有可能性。量子理论建立了一个人们既不能思考也无法通过感官感觉到的现实,但是可以从它们的算法开始理解。这是建立在理论上的一门科学,带着这个发现,这种理论将保证我们既无法直接地也无法想象地获取的现实的存在。
即使精神分析继续在一部分“公众”那里产生比对量子力学更多的抵抗,在物理学中通常承认为真的东西,在精神分析中也是真的。
分析的理论也注意到一个由弗洛伊德所称的压抑引起的、不是直接经验的现实。他称这个现实为精神的现实,并且它是从与转移相关的效果中推断出来的。
只要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证明不出这个“物”除了它的效果之外以别的方式存在,并且有可能以全新的解读来理解这些效果,就能断定对言说的存在来说非常根本的某物存在,这个可能性就是弗洛伊德的挑战。况且弗洛伊德发明的这个解读是如此之新,以至于正如我刚才对你们所说,从他最初试图公开报告他的经验时就遇到了巨大的抵抗。
谈论无意识的巨大困难,尤其是这个困难引起的抵抗还与弗洛伊德的发现对源自原始神话的、甚至是科学的日常思维所激起的后果相连。这很容易描述。例如对于 “拉康”派的旗帜之一的客体小a,我们学着结结巴巴地说:“口腔客体、肛门客体等等。”甚至是欲望的客体。多大的误解啊!
尽管他所考虑的客体是我们欲望生活的中心,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当拉康说:“我们不相信客体,然而我们确认欲望,我们从对欲望的这个确认归纳出这个可以说是客观的原因”的时候,清楚地说了这一点。
为了从科学上,即从理论上理解那些临床事实而重视演绎逻辑,从最开始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有。然而正是拉康给了欲望所有的重要性,并且他为理解精神分析经验打开了思考空间。
如果在分给我的时间里到了我讲话的最后,你们会看到由拉康再加工和明确表达的“弗洛伊德的发现”带领分析中的主体认识到,从这个位置的现实出发他决定仅仅放置一个大彼者的一句话,并且是在他自己的思维之外。
为了更清楚些,我说每个分析者揭示出来的东西正是在被读、即被说之前先要被写,站在自由选择的立场上就他的命运来说,这大大缩减了他行动的选择余地。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在分析中说话的主体看作是一个文字与一个解读之间“有益”碰撞的效果!拉康以近乎粗鲁的方式灌输给他的听众的东西是:
“ [……]在那里每个主体都被告知他总是而且从来只是一个假设!”还有“ [……]因为主体从来仅仅是假设的”。
一个主体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解读的效果,是源自一个已经写下的文本(一句“话dire”)的一个“说dit”,这个观点在拉康那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表达出来了,尽管不是同样清楚。这个想法把主体等同于一个“量子的客体”……然而我只是说“等同于”。
仅仅是“等同于”,因为人类是在自然 [3] 中,即生物学地存在着。然而这种具有早产特点的哺乳动物,只有在他和一种把他与他的、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的“自然”永远切分了的言说的相遇中才能成为真正属于“人类”这个物种的“人”。当他是早产的时候,因为与大彼者的能指的相遇,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哺乳动物,成为一个冲动的哺乳动物,而再也不是受本能驱动的哺乳动物。在拉康说 “冲动,是因一句话而有的身体中的回声” 的范围内,这是他苦恼的开始。多么重要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运行在他的身体层面上!
在自然思想中,存在着把人类看做是皮质化的、能自然地或很好地适应环境的生物学动物的观点。
然而这不意味着人的真性并不存在, 我答应你们在我发言的最后我试着给出一个可能的答案。我提前向你们指出,仅仅只有涉及到人类时,为了定义他们,我们才可以把“真正”和“自然”并置,而这不是多余的……
我刚刚对你们说的所有东西与把我们聚到一起的问题相比可能有些离题。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我相信,我们处在这些天里鼓舞你们每个人的问题的中心。
事实上,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那么由弗洛伊德制作来理解精神分析经验的理论就应该是普遍的。因此在中国也应当有效。
相反,如果从一个相同的经验(精神分析)出发,你们建立了一个不同的理论,那么,由于它的言语,中国文化就成了破坏弗洛伊德说的具有普遍使命的理论的可能例外。它就把这个理论减缩为只在西方有效的理论。
你们看,你们在这个讨论中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
因此为了能够说这涉及一个普遍的经验——精神分析,我们现在就要关心我认为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中国也应该有:
1、应该有一个说话的人,并且我想不到这第一个条件怎么能不是普遍适用的……在中国也一样。
实际上,人类存在的所有地方……也存在抱怨。因此就有潜在的分析者。抱怨的重要性早在拉康定义精神分析为一个“被引导的妄想狂 paranoïa dirigée 时就被他所强调。
我还相信总有人相信在某处有大彼者对他的不幸负责,并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我们已经可以指出,一旦他作为大彼者的存在被提出来讨论,毫无例外,大彼者(上帝、祖先等等)向我们要求着什么东西这样一个信仰在分析结束时就可以崩溃。我甚至认为这是分析的“目的”之一。
我给你们讲讲大彼者,毫无疑问,我要详细解释拉康的这个术语。
我们说大彼者与一个和话语有非常紧密联系的“彼处”对应。正是从这个彼处出发,我们学着在分析中辨别方向,以便对主体的位置(我们被大彼者传唤到这个位置,以便存在)有一点理解。正是在这个地点可以破译出有关我们存在的一些东西。正是从这个地点出发,我们才有可能保证我们作为冲动性的生活回应我们的冲动性的、即属于欲望的生活……
把我发言的结尾提前些,我想说这个彼处与一个书写混合在一起。如果想要它给我们揭示我们开始说话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该学着阅读它。这即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显得非常中国式的拉康告诉我们的、我们从那里开始外存在 [4] 的位置。
为了把这给你们解释清楚,我发现自己也完全是中国式的了(在我所能理解的东西里,在你们的言语中被占据的地点可以表示存在),然而同时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说是“弗洛伊德式的”,我在那复述的是弗洛伊德古老的、不变的隐喻,他把精神分析的工作和考古学的工作对质起来。
而且如果由于读者读这个文字的不可能性,或者是与这个文字自身相连的可能解读的缺乏,它没有被读到,它就纠缠于拉康以“实在”命名的维度,那么在某种条件下,这可能在它居住的人那里引发精神病。
尽管书写能被读到, 然而如果它没有留下空缺的位置以便向读者揭示其主体位置的话,它就成了纯粹描述性的或可数的并且仅仅只能揭示现实层面,如同拉康在以《电视》为名发布的电视采访中所说的“实在界的鬼脸”。
为了给你们解释我想对你们说的东西,我让你们回想弗洛伊德对他的一个访客的回答,这位访客称赞他的勇气以及没有因折磨他的疾病而显出抱怨的表情。弗洛伊德对他说:“您知道,我很想抱怨,但是我不知道能对谁……”还有什么比他停止要求大彼者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更好的说法呢,而这正是所有分析者表达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可以持续很久!
更确切地说,他把他的抱怨(癌症以及相应的痛苦)的动机归到实在界,对此,任何符号性都无法回答,而且没有任何关于主体的东西能够显示出来。他愿意以巨大的勇气忍受实在界存在,没有能够读懂它,并且给它一个意义的特别的收件人。
2、应该有一个在听的精神分析家。
在那里,马上就复杂了。因为我没有说“在听的某个人”,这个人给看门人或同情的朋友留着空位。不,自从来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就知道需要精神分析家在这个位置。况且弗利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充当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家。然而他被弗洛伊德放在了“假设知道”的位置上,而这对弗洛伊德来说就足够了。当弗利斯放弃这些的时候,弗洛伊德是不愿意的。
3、这个说话和抱怨的人应该为他的治疗付费。我不认为付费的必要性仅仅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效果,因为它的角色尤其是“技术性的”。它上演了,我甚至说是“做出”了对所有言在来说的债务问题。
原谅我没有提前介绍就使用拉康的“言在”这个术语,但是我没想出在这里如何避免它。
实际上我不能说“对每一个说话的人来说”,因为说话的人的共同命运只能是“高谈阔论”以便不冒“言在”的险。然而在治疗经验中,他们通过他们的分析家而被贷给存在,甚至不顾他们的反对。我认为支撑这个来自分析家的挑战的东西一部分是拉康以“分析家的欲望”来命名的东西。欲望在接近分析结束时应该朝向别处,他的病人不是自认为受害者而是颠倒了他的命题并且感到欠了债。
我们在街上或者社交领域所是的言者,绝不可能通过话语来冒险提出他们“在世上存在”的问题。这将假设,在他们说的东西与他们认为说的东西及定义他们的东西之间的切口是要被辨认出来的,此切口不与大彼者的恶意相连,而是与说话(即使是为了抱怨)的可能性共存。
为了更好地理解切口这个问题,我说它是每一个分析者在他受分析家的邀请而勇于“说所有他想到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在他的分析中经历到的东西,并且事后他会发现“所有他想到的东西”仅仅是大段的废话,然而必须通过这些废话,不知不觉地从这些废话的意义的偏差及失败开始,对在他身上所想的东西有一点概念。这个分析者将会发现,正是在他思想表达的失败中,因此是在他说的话中,他进入真正在他身上所想的东西中。并且这个发现总是在他发觉他不在他认为所处的及所说的地方的时候出现。陈述的主体发现,尽管他认为是在说,然而他是被说。
因此与语言共存的这个切口(我认为我们稍后有机会谈论它)是撤销了可能支撑他的、甚至是可能使他依靠其信仰而存在的所有想象位置的东西。
同时这个切口从他除了定义自己为在当前时刻的缺席之外做其他定义的不可能性出发,把他定为真实地活着;如同他存在于那里的一个时刻的一个事后可见的痕迹。
我认为你们能感觉到,通过这么说,我肯定“现象学地”言说、言说的存在不是如此登陆在“自然”的秩序中, 自然的秩序是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以其直接性在场的。人类,他作为主体,通过他言说的存在的特征,被与这个直接性切断了。
我知道这点显得多么让人难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提醒你们精神分析(如果我们把《释梦》看做它真正开始的文章)诞生于普朗克发表他关于“黑体光谱”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认为是量子物理的诞生)的同一年 !甚至,我让你们随意想想,在我看来与《释梦》相比如此创新和革命的《超越快乐原则》这篇文章,出版于关于量子物理的公式体系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年(1920).而这两门学科,精神分析和量子力学,除了它们的生日相同以外,还有一点相同,即它们都与不能被表达的东西打交道,如同我刚才所说,正是在那里出现了接受它们所谈论的、然而紧贴我们的世界的困难。
存在的无意识只能通过在治疗经验中揭示出来的效果而被推断出来,并且它(无意识)涉及“不思考”(拉康的文字游戏,我不知道能不能翻译出来)而不是“思考” [5]。我邀请你们在这里,对先前Guy Flecher关于必须与交流领域区分的话语领域的主题对我们说的东西给出你们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一个迂回的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在随后的讨论中折回“人类的本性”的问题,至少我这么希望。
相对于这个区分,我请求你们更进一步:话语/交流是重要的东西,必须将重要性赋予切口及其位置,它属于我刚刚试图向你们表达的结构。 至少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一个精神分析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并非心血来潮地使用“结构”这个词,而是参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及对其作品的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试着回答我们对言说的存在之真性的问题。
我们确实知道属于“自然”秩序的东西是普遍的,而属于文化秩序的东西是特殊的。
然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他对各种各样的文明的神话研究(我简洁地说!)能够证明,所说的作为乱伦禁止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普遍的。这是所有文化的一个不变量!因此就该把它归到“自然秩序”那边……然而当然不是这样。再回到Guy Flecher的发言,狗不知道乱伦。狼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理解这,即把这个禁止放在一个可能有交流的生命世界中的唯一方式是,正是这个不让这些自然王国的生命进入文化王国。而这不就是一个切口!
我们是通过切口成为人类的!
—好吧,我觉得这会显得是一个徒劳无用的空谈,为了喘口气,再让你们思考一下,我给你们提一个我不知道答案的简单问题。让自然进入文化或是在切开博罗米结的一个绳圈时把圆弄散的这个切口……来自哪里?谁引起了它?而如果文字像我认为的那样原始,那么抄写人又在哪里?
或者是否他的文章的解读使得抄写人存在?
那么他的文字呢?
庄子非常富有诗意地揭示的关于梦蝶的古老困境,如果我的记性不错的话……
是否因为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以至于弗洛伊德用他的原始游牧民族的父亲的故事来给原始神话留出一个位置?或者,问题和答案是否莫比乌斯式地结在一起,如同我刚才试着指出的?莫比乌斯式即“没有那个就没有这个”。
好吧,消遣结束了……
无论如何,我再说一次,这个切口通过早产的人类小孩被能指轰炸的事实得以产生,这有一个效果:债务、符号、想象和实在形成了。
由此它把我和交流的世界,或者对等的被陈述主体及陈述主体永远切断了:这是符号的债务。
它把我和对在包围我的自然世界中的我的(生物学的)身体的适应的所有固有经验都切断了:这是想象的债务。
它把我和享乐经验的综合功能切断了,而似乎所有拥有生命的身体都有享受它的权利:这是实在的债务。
这个切口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效果,并且我们的文明认定它为悲惨的,因为它最终给了我们“存在的债务”,并且这个债务不是“可以偿还的”,而且也只能传给后代。
如同我们的诗人兰波所说:“我是一个彼者”,而这很难承受。
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提出这第三个与最低要求有关的条件,以便我们确实谈论相同的经验:精神分析。
因此,在西方,不会把使一个精神分析可以进行的东西和心理疗法混淆起来。
然而我认为你们已经发现,主要是第二点引起问题。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一点假定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要求来说是事先“可能存在的”。而我相信,想知道是否真的面对一个分析家,对每一个试图寻找一个可以相信的个人的分析者来说都是合理的问题。
分析的团体试图通过把文凭或者保证奖章授予通过了制度程序的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徒劳的。
然而我认为,在一个如此这般运作的机构中,仅仅只给言说的人(我刚刚在我的第三点中对你们谈到了我对它的看法)留了位置。
不断地重复和弗洛伊德时代在维也纳的“星期三聚会”相同的时刻是重要的,以便每个人在他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可以各自前进,就个人而言,我被这说服了,即使这太天真。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说,赌注就在于足够直接地与精神分析从每个言在的背后赶出的新的、不可信的东西相遇,而这在我看来正是根本的东西。
因此,你们尤其不要太快地制度化!我的一点经验告诉我,对于所有制度关系来说,我们会受益于尽可能长的时间地限于“工作的转移”。
况且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时刻的经验中获得的东西。
我没有忘记,在这个时刻我是被叫来研究“言在之真性”的。而且它很好地向我表明它涉及的是孟子对我们说的“言说的存在”。
那么,在我们所处的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同意,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我认为我们感兴趣的这个“言说的存在”维持着与我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言在的最紧密的关系是正确的。
在分析的经验中显露出来的言说的存在、言在,我再进一步,以及主体,在我对你们讲话的这个时刻,我把它们等同起来。
既然它是从与自然的切口中产生的,那么什么是它的如此特别的本性?
是不是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又回避了它?
因为通过问什么是它的本性我就给了它一个,然而不是自动地与我们通常听到的(至少在西方)本性相关。
我希望你们还清楚地记得在这个发言的第一部分,精神分析家关心的言说的存在与自然的距离甚至和天与地的距离一样远……在一个和另一个的边缘都有变动的天际、边界,在那里它们的命运似乎融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告诉想要一个保证他的、确定的位置的人,如同天际,主体是一个虚构。这是一个言说的生命,既不是天(咿呀言语)也不是地或海(自然),而是两者之间的海滨或天际,正如我们期望的!
如果说我刚刚给你们讲了量子世界的发现和无意识的发现在日期上相似,这也是因为,再现弗洛伊德称为“schauplatz(场所)”的、用来指代无意识的这个“世界”的困难,在我看来在这两个情况下都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对一个新的、不可想象的世界的艰难探索那里,我们过去全部的标记、确信都应该被抛弃。另外你们顺便注意一下 “schauplatz” 这个术语把无意识变成一个注视我们的地点(这里有一个法语的文字游戏),这多么有趣。我真的相信是通过和刚才那个词一样的词汇的细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前进。通过给予这些细节其全部重要性!
实际上有多少分析者带着应该去“看”什么和试图治愈折磨他的疾病有关的信念而开始一个分析呢。
对听懂最好是“如同我们被看那样去看,即书写”,对抵达我们这里的东西有所理解来说,这些时刻都是必须的!
简言之,这个无意识世界是一个与我们学着多少科学地总结的“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并且我们已经按我们所有的推测来形容它了。
至少在西方,我们曾按照这个自然观点学着放置和思考我们的存在,这个观点是如此地充浸着我们,以至于对我们来说,不在一个与它有关的自我评估系统中思考总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更好地向你们说明承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个 andere schauplatz(彼场所)占据我们、注视我们,并且尽管我们的命运正是在那里上演,然而我们从来不可能真正进入其中)存在的困难(现在还是困难),举个例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拉康的概念“大彼者,能指的宝库”的一个常见的变形。在某些分析家(我们有时当然避不开这种团体)的口中,这个概念变成一种包含了在语言中可用的所指的整体的巨大词典,并且为了我们相互理解,使它存在就足够了。新的误认 Misunderstanding !
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拉康更喜欢用“咿呀言语 lalangue ”这个术语而不是“语言”这个术语?
是为了避免我们从另一方面知道的无法避免的这种滑动?
因为这个令人感到舒服的,所以对所指来说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知,它作为被回忆起的客体的复现表象而存在,并且它根本不需要一个主体以便存在。
然而,就像我刚才对你们说的那样,精神分析正是把我们从这个舒适那里赶走。而且正是因为它把我们从这个舒适那里赶走,我们才无法认定说它的首要目的是治愈我们!我相信也正是因为这,弗洛伊德才能说我们无法分析富人。在最可消耗的客体的形式下,求助于所指的可能性在他那里是太在场了。
所指如此这般地即孤立地存在。这并不是能指的情况,如此这般的能指并不存在,正如孤立的量子“粒子”并不存在。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系列的能指(即一个一个相加的能指的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于陈述的展开中而使主体存在。
并且为了产生这个主体,要遵守弗洛伊德在《释梦》中阐述的语言法则——凝缩和移置。
相对与交流相混淆的意义而言,这些法则每次都会引起一股切口,而弗洛伊德的第一批“标准”文本仅仅只是谈这个!
在我内心深处,我想象(然而想象不等于确定)对所有说话的人,或进一步,对所有接受“被说”的人来说,尝试这个分析经验都是可能的。在法国,我们有一个歧义的表达,我很喜欢用在我的病人那里,它在于让他们说,甚至让他们重复:“您随便被说( laissez vous parlé )”,他们总是听成“您随便说(laissez vous parler ) [6]”,控制的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地被重视。
因此我向你们,中国同事,提出开头的问题:你们独特的语言模式能产生什么样的无意识?切口在你们的辞说的哪个层面产生?
语言的差别,与精神分析的发明相比你们语言的结构的差别,是否在某个层面修改了这个经验的发现?受益于这个经验,它是否通向一个新的理论,我非常想要知道。
因为,就我对你们的文字的那一点点了解,如在 lacanchine.com 网站上所讨论的,你们已经超前我们几个世纪了!
简而言之,我告诉你们,读这些在 lacanchine.com 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时,常常让我觉得你们的言语很久以来就已经有了对发明精神分析来说所有的成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为智慧(Sagesse)的东西你们已经发明了!为什么?
这是否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就我所能知道的,自15世纪以来,你们的皇帝凿沉(或烧掉?)他的舰队来避免根本的彼者不会在天朝的寂静中引发骚乱,如同我所能看出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的答案当然会给你们要克服的困难一点点意见,这个困难是为了给予精神分析这个如此震动人心的经验以引入你们如此伟大的国家的权利时遇到的。
我很想知道,按照你们的语言,如同我们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是否精神分析的经验必然产生一个服从于逻辑的、被陈述(然而是在别处被陈述)的 “我”。
一个没有陈述的必要性的“我”。
一个仅仅只能书写地存在的“我”,例如和在梦中的情形一样。
你们现在看到了为什么我对你们说我觉得你们有一些超前!我相信在这个没有陈述的、仅仅书写地存在的主体,很久以来都是你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你们的文化中“存在”这个动词通过一个地点指示被表达出来!你们现在理解为什么我如此强调用弗洛伊德的术语“Schauplatz”来指无意识了吧。至于这个设想,可以说我的一点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现在直接到告子和孟子的这个争论,它被翻译成:
你在话语中找不到的,
你在心里也找不到,
你在心里找不到的,
你在气中也找不到,
告子
以及:
你在话语中找不到的
你可以在心里找到
你在心里找不到的
你在气中也找不到
孟子 [7]
正是对必要的语言规律的服从——以便给一个人随后就可以参考的东西以一个意义——造成告子表面上有理由反对孟子。
然而我们还可以说,当孟子回答“你在话语中早不到的东西,你可以在心里找到”的时候,孟子比告子走的更远,只要设想他说的“心”与拉康的实在有着最紧密联系。
此外,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孟子给了道德感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人类存在的状态。他给它一个由言语(问号)强加的、在所有的政治或社会干涉之前的逻辑时间,以便主体存在。而这样,他说的话就和告子说的不同。
通过把人变得与组成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无关,他结合或发明了一个更宽泛的人类存在的概念。
如果是这样,孟子与其说是一个道德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伦理学家”。至少在孟子暗含地承认伦理是一个从咿呀言语推出的逻辑位置,而且这位置由言在掌握,以便言在能取得他所有的坚固和尊严的意义上。
极端地说,并且我相信这是拉康的立场,仅仅只有作为对咿呀言语的根本服从的伦理。
从西方的观点看,正是因为这,伦理具有普遍的天命。
我想顺便谈谈,我觉得孟子与告子的这个讨论对我们这个正建立在“……的权利”基础上的文明来说多么有现实意义,这即是说,它求助于外在秩序,并且经常是求助于新自由主义契约来调节!
我刚刚跟你们谈了伦理,然而我认识到我没有很好地向你们解释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实践来说是基本的,并且和“言在之性”有最紧密的关系。
无论如何,当我们谈论“言在之真性”、天际或海滨的时候,我确定,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置在伦理的旗帜下,因为它构成了回答的一部分。
唯一有力的说法是:从最开始,对咿呀言语的服从是使我们真正地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条件。
伦理立场在于让我们服从可以被阅读的咿呀言语的一个效果,并且在于接受这些击中我们身体的效果。
为了给我们的相遇题名,我觉得有必要就我刚刚对你们讲过的东西再讲详细些:“从最开始,我们就服从于咿呀言语的存在以便存在。”
我明确指出,我们当然是通过服从于咿呀言语来作为一个“言说的存在”而存在。
我们愿意明确地说,正是咿呀言语把我们变成主体!从那以后,只有咿呀言语能回答我们关于在自然之中及之外的言在的独特位置。
以非常根本的、因此是挑衅的方式,我断言,咿呀言语更多属于自然而非言说的存在!
此外,在我们西方文化中,有一个讲述这点的合适故事。它叫《安提戈涅》。这是一部由公元前5世纪一位希腊人写的悲剧。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它几乎是提出了与孟子和告子之间争吵的相同问题。此外,拉康在他关于伦理的讨论班上把它作为支柱。
这部戏剧上演了一个老国王,互相争斗而死的国王的儿子们,一个自杀的母亲等等的故事。女主角是安提戈涅。
为什么?
简单说是因为,在这部剧中她是唯一一个不以道德方式行动的人。
她既不按照她的地位,也不按照国王给的命令行动,而对于这些命令,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遵守,以便控制城邦的秩序。
不,在面对权威及其道德(后者甚至被赋予了最好的意图)时,她表现为一个意识到这种“言说的存在”的脆弱性的人。为了服从话语的法则,她放弃了所有由“自然”带来的乐趣,这个服从使她真正地作为安提戈涅存在。
最后,把大彼者从折向小彼者中救出,也是通过这,她把城邦(在这里即是人性)从语言的纯粹功利主义的用途中解救出来。
以她的生命为代价,更确切说是以放弃某种“自然的”、在她那里肯定是舒适的某种生活为代价,安提戈涅维护了一个没有排除意义的缺席和诗意的生活存在的可能性。
她给生活保存了一个反对语言霸权(它仅仅是物的清单,并且为了拥有活着的“权利”我们就要迫使我们屈服于它)的未来。
她用她的生命得到了正是我刚刚对你们说的“不”交给我们“言说的——生命” 的证明。
在她的故事的那个时刻,她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接受死亡,被用于管理一个并不参照于“天条”的世界秩序的道德定罪。
通过她的行为她表现出有生命力的,不是作为隶属于自然的生物学身体,而是更为根本地如同“言说的存在”一样有生命的——“言说的存在”的真正生活取决于咿呀言语对自然的优先权的确定。
由此我到了报告的第三部分。
为了引入这第三个部分,我请你们回想一下,在第一部分中我曾问你们分析经验的普遍与否。我通过特别强调这是话语的一个经验,话语在冒险的这个人那里产生了某些转移的效果,并且强迫他承认他在使之存在的咿呀言语那里获得的符号债务,来对你们说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经验。
我还被引导去说明,通过把人类与其动物自然性切断而把他造成言在,言语在人类身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言语怎样把他与某种想象的一致性(即其存在与物之世界的一致)永远隔开。
为了让这更清楚,产生言在的这个言语与交流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无论如何它都不是“自然的”,而且它来自一个全部被称为无意识的地点,我曾紧跟拉康建议你们以单独一个词、咿呀言语来称呼它。
然而,从言语到咿呀言语的过渡有着这么一个根本的东西,它是我们在实践中放弃道德向导,以便伦理向导指引我们。对于担当某人的精神分析家这个任务来说,亲切和绅士是不够的。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应该选择孟子!
我希望我也给你们指出了我们言说的存在的位置有多么脆弱和敏感,随时都能降低至拉康称为“训从的( d’hommestique)一个动物的位置!况且正是根本的和首要的伦理错误能够造就一个人!向这个“训从( d’hommestication)让步!我希望这个词可以写成中文 [8]。
最后,我还希望能够让你们触及,我描写的言说的存在的这个如此脆弱的位置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世界中唯一的财富。安提戈涅,美丽的、卓越的、脆弱的安提戈涅告诉了我们,为了如这个叫做言在的特别动物一样在自然中存在,有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无论如何那就是我如何终于来到我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安提戈涅保卫的东西,难道不就是“言在之真性”吗?
难道这不是她宁死也不愿抛弃的东西吗?
然而每一个来给一个分析家说真心话的分析者不也处在安提戈涅的位置上吗?他们不是也没有断言话语对整个物的世界的优先权吗?当然,最终他们并没有死!然而是否如此肯定,某个在他们身上没有死亡的某物让他们觉得活着?
总之,对一个有着尝试向一个分析家解释他服从一个咿呀言语的后果,以便治愈某些神经症症状的经验的分析者来说,这个经验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我相信这正是对分析家来说的一个根本问题,并且它意味着任凭研究使他存在的咿呀言语的嗜好的带领,他带领他的分析到一个关键点,在那里他危及他的人类存在 !
如果他没有走这条路,我想他一生都只是一个心理治疗师……!
实际上,你们完全可以在分析家们之间发现这个切口。
在“对抗”告子的分析家和“对抗”孟子的分析家之间。
为了判断精神分析的结束,有人坚持弗洛伊德的观点,当分析撞到“阉割的岩石”时这个结束达成。只要把这个岩石看成如同一堵墙,在墙那边没有任何东西语言能够理解;如同对所有可能的解释的一个界限。
再者,有人考虑,是否有分析可能在那个时刻存在一个解释的空间?
我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他有很长时间都被说成是“编造”了图腾、原始游牧部落的父亲、可能也包括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谈到的死亡冲动,等等。然而,这些理论进展构成了他的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他非常珍视它们。
我认为,事实上,这些进展试图以逻辑的方式理解他知觉到的而不能命名的,却又在这个岩石背后起作用的东西。
而我发现这个知觉,这个在鞋里的石子,从他的著作的最开始,当他在《释梦》中谈梦脐、解释的极限的时候就一直纠缠着他。
拉康把在岩石那边的这个东西命名为实在,这是他的几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且他狂热地对其感兴趣。
我相信,说随着他的教学、而且也随着他的分析治疗的教导逐渐反映出治疗正是对准实在的问题,是毫不夸张的。我不是说我们要丢开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节、认同、单划(le trait unaire)、阉割等等的贡献有关的所有东西而不管;不,我要说多亏拉康,我们才敢于在弗洛伊德说分析停住的地方继续分析。
此外,由此分析比之前持续的时间更长。
全面赶上弗洛伊德然而同时超越弗洛伊德是拉康的巨大任务。你们,我们应该信任的新一代的任务无疑就是“全面赶上弗洛伊德、拉康同时也要超越他们”。
总之,我非常指望你们能惊到我们,甚至可以吓我们一下。
当然,当我说“超过”,这意味着要对直到拉康的生命的结束、实践的结束的时候都纠缠他的东西有点概念。
而这,我相信它完全是“中国式的”的,至少就我而言,我可以设想 “中国式的存在”。
我可以就此对你们说两句,因为我相信你们已经充分地标记了这条路,我认为拉康最终认为(或者敢于说)从根本上我们被“书写( Écrits)”早于被说!!!!
想一想《文集(Écrits)》是唯一一本他独自署名的书。
直到他实践结束,拉康都按照本义来理解弗洛伊德的“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然而他从一个非常坚定的翻译:“ Là où “ça” était, Je doiT (avec un T !) advenir [9]”中得出所有结论。
这种翻译方式(用t而不是s [10])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结束,因此是对人类的真性的认识来说,分析家在他自己的治疗结束时,就知道在对言在(他也是没有疯掉的被说的存在)的真性的认识方面选取一个坚定的方向。这是一个认出自己的一个命运的“我”,然而他不认同于他自己。
而这正是我最终想到达的,我事后认识到我知道应当对你们这么说它,你们提出了“言在之真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应当对作为我的通过者的你们说这些。这个问题只在它的返回中找到答案。
同样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言说存在什么时候表达出他的真性?
我相信我的回答不会冒犯你们:作为无意识的产物的言说存在,只有在他接受他的言在的位置的时候才能表达他的真性。
正是当他接受了只有活着,而且只有在他没有进入的、然而是在他的存在深处的一个彼处那里才能认识言说主体的这个风险以后,他才贴合他的言在之真性。
正是当他被为了存在,除去占据一个伦理的位置以外别无选择的确信占据的时候,他才处于“言在之真性”的领域。
正是当他承认为了在其“言在之真性”中存在而欠了咿呀言语的债,并且完全承担这个债务的时候,他才是一个配得上这个名字的有生命力的言者。
正是当他接受坚持这个不是选择的选择的时候(如同安提戈涅的勇敢行为),他承担了他的“言在之真性”。
正是当他拒绝把从来只能在他话语的失败中被言说看作一种痛苦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活着。
在实在以一个神奇的数字(它示意我应该停下来)的形式被中国化的这一刻,我留下最后的话。在这一刻,这篇文章用了8888个词!